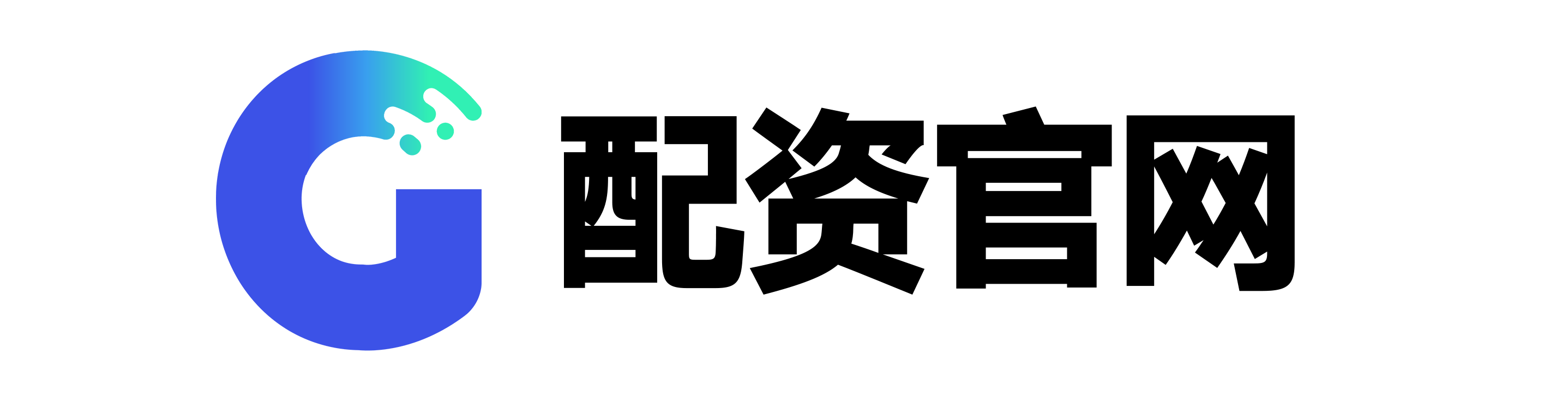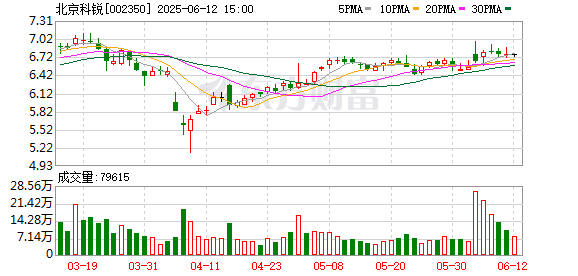配资网站查询 93年我偷偷摆摊卖烤鸭,被未婚妻发现,她拧我耳朵:还逃不(一)

一九九三年的春天配资网站查询,风里还裹着去年冬天的料峭,像个舍不得走的老倔头,一阵阵往人脖领子里灌。我缩着脖子,守着我那辆二八大杠改装的烤鸭摊子,就在县城唯一那家红星电影院的斜对面。
车后座两边挂着铁皮箱子,里头是我的营生——七八只油光汪亮、焦糖色的烤鸭。油脂滴在下头的小炭炉上,时不时“刺啦”一声,爆起一小团带着焦香的白烟,这味道混在电影院门口瓜子、香烟和劣质雪花膏的空气里,也算独树一帜。
我跺了跺脚,帆布鞋头都快磨破了,沾着一层灰扑扑的尘土。这地方好,人来人往,而且离我们村足有三十里地,安全。安全的意思就是,离郑丽华远。
郑丽华。这名字像颗小钉子,轻轻巧巧就扎进我心窝里,不深,但你就是忘不了,一动弹就隐隐约约地提醒你它的存在。
她是我的未婚妻。说出来都他妈烫嘴。什么年头了,还兴这个?可我们那儿就兴,兴得理直气壮。据我娘说,穿开裆裤那会儿,两家大人指着还在尿炕的我们俩,就这么定下了。她家挨着我家,中间就隔着一堵矮土墙,墙头年年爬满牵牛花,紫的粉的,开得没心没肺,像她小时候咧开缺牙巴笑的样子。
可人是会变的。女大十八变,她越变越扎眼,是那种能把年画上的仙女比下去的漂亮,眉毛黑,眼睛亮,一根粗黑的大辫子在身后甩,腰是腰,腿是腿。可她那脾气,也跟她模样一样,越来越“出众”,泼辣得像我们地里最红最辣的那茬朝天椒。小时候跟人打架,她冲在前头,辫子一甩,指甲就往人脸上挠。长大了,管起我来,那更是无法无天。
展开剩余92%我穿什么衣服,她管。“刘大年,你这件褂子都洗败色了,像从咸菜缸里捞出来的,赶紧换了!”我跟哪个哥们儿多喝了两杯,她管,能直接从饭馆子里把我揪出来,当着一条街人的面数落。我看她一眼,她眼睛一瞪,比村支书还有威严:“看什么看?我说错了?”
我烦,我真烦。我才二十二,感觉活得像她手底下的一个兵,还是那种永远不合格、天天挨训的后进兵。我爹妈还总向着她,说丽华是为了你好,是个过日子的人。这日子我过不了。所以,我跑了。揣着偷偷攒下的百十来块钱,蹬着这辆破自行车,跑到县城,支起了这个烤鸭摊。
自由。这就是自由的味道,虽然混着烤鸭的油腻和街角的尘土,但吸到肺里,是畅快的。
“喂,卖烤鸭的,来半只!”
一个穿着西装,头发抹得锃亮的小年轻搂着个姑娘走过来,看样子是刚看完电影。我赶紧应了一声,手忙脚乱地剁鸭子。刀砍在砧板上,梆梆响。我这手艺是跟一个远房表叔胡乱学的,糊口而已。
正低着头忙活,忽然听见旁边几个摆摊的老娘们在唠嗑。
“听说了没?就今儿个,东头老徐家娶媳妇,就是纺织厂那个徐志刚!”
“哟,那可是大喜事!他家阔气,席面肯定不差。”
“那可不,请了不少人呢……”一个声音压低了些,带着点神秘的兴奋,“我听说啊,咱这片儿好几个老同学都去,就以前常在一块玩儿的那几个……”
我的刀顿了一下,心里咯噔。徐志刚?他跟我小学还是初中同学来着?好像还同桌过。郑丽华……她跟徐志刚他妹好像是朋友?
心口那颗小钉子,好像被人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。
不会的,县城说大不大,说小也不小,哪能那么巧?我用力甩甩头,像是要把这念头甩出去。郑丽华在村里呢,她没事跑县城来参加什么婚礼?她肯定不知道我在这儿。
可一整天,我这心就跟放在小火上慢炖的鸭子似的,七上八下,不得安生。收摊的时候,太阳已经西斜,把天空染成一种暖昧的橘红色。我推着车子,慢吞吞地往我租的那个四面漏风的小破屋走。路过东街那家算是县城最高档的“悦来饭店”时,果然看见门口扎着大红绸子,贴着硕大的喜字,人来人往,喧闹声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。
我脚步没停,甚至没敢往那边多看一眼,加快速度走了过去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躲远点,再躲远点。
第二天,我照常出摊。阳光比前一天好了些,暖烘烘地照在背上。也许是我多心了。世界这么大,哪能说碰上就碰上。我心情稍微放松了些,甚至跟着电影院喇叭里放的“妹妹你坐船头”哼了两句。
快到中午,一个以前在村里玩得还不错的哥们儿,骑着自行车“叮铃铃”停在我摊子前。
“大年!真你小子啊!我还以为看错了!”他跳下车,一脸惊喜。
我心里有点发虚,讪笑着:“啊,混口饭吃。你咋来了?”
“我来吃酒席啊!徐志刚结婚!走,一起进去喝两杯!好多老同学都在里头呢!”他说着就要拉我。
我像被火烫了似的,猛地往后一缩,差点带倒我的烤鸭箱子。“不去不去!我……我这儿忙着呢,走不开!”
“忙啥呀,这都饭点了,谁还买烤鸭?走走走,给你小子改善改善伙食!”他不依不饶。
“真不去!”我死死攥着我的自行车把,像攥着救命稻草,“我跟他们……不熟。”
哥们儿狐疑地看了我一眼,又看看我的烤鸭摊,似乎明白了点什么,脸上那热络劲儿淡了下去:“哦……那行吧。那你……忙着。”他推着车,一步三回头地往饭店走去。
看着他消失在饭店门口,我才长长松了口气,后背竟然出了一层薄汗。吓死我了。
我定了定神,决定今天早点收摊,避避风头。正要动手收拾,又一个声音响起来,带着点不确定:“刘……大年?”
我头皮一炸,这声音有点熟,但不是郑丽华。我僵硬地转过身。是王娟,郑丽华的一个小姐妹,以前老来我家找她玩。
完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王娟确认是我,脸上露出夸张的表情:“哎呀!真是你啊大年!你咋在这儿卖烤鸭呢?丽华知道不?”
我喉咙发干,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:“啊……随便弄弄。你……你别告诉她。”
王娟眼神古怪地在我和我的烤鸭摊上来回扫了几遍,嘴角似笑非笑:“哦……我进去吃饭了,志刚结婚。”她特意加重了“志刚结婚”几个字,扭着腰走了。
她肯定要告诉郑丽华。她那张嘴,从来就兜不住话。
我站在原地,手脚冰凉。刚才那点阳光,此刻照在身上,只觉得燥热难当。跑?现在推着车子跑?会不会更显得做贼心虚?
就这么一会儿功夫,好像老天爷故意耍我似的,饭店门口那片喧闹声陡然拔高,像是宴席散了。人流开始涌出来,男男女女,个个脸上带着酒足饭饱的红光和笑意。
我慌忙背过身,假装低头整理铁皮箱里的烤鸭,心脏“咚咚咚”地擂鼓,恨不得把脑袋塞进箱子里去。耳朵却竖得老高,捕捉着身后的每一个声音。
脚步声,谈笑声,自行车铃声……混杂在一起。没有那个我害怕听到的、又清又亮的女声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人流渐渐稀疏。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点。
也许……没事了?王娟可能光顾着吃饭,忘了?或者,她还没来得及说?
我慢慢直起腰,偷偷吁了口气。
就在这口气吁到一半的时候,一只温热、带着薄茧的手,猝不及防地,精准无比地,拧住了我的右耳。
力道不轻,带着熟悉的、不容置疑的掌控感。
紧接着,那个我躲了两个月、梦里都能把我吓醒的声音,贴着我耳根子,带着一股子压抑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,响了起来:
“刘大年!我看你还往哪儿逃?!”
我浑身一僵,那半口气卡在喉咙里,差点没背过去。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周围还没完全散尽的老同学、看热闹的路人,“哄”地一下全笑了。那笑声像滚开的油,泼在我脸上,火辣辣的。
耳朵上的疼,脸上的烫,心里的慌,拧成了一股绳,勒得我喘不过气。羞恼像野草一样疯长,我猛地一甩头,想挣脱那只手,嘴里不管不顾地嚷道:“郑丽华!你放开!大庭广众的,你像什么样子!谁要跟你结婚了!我告诉你,我……”
我后面那些更混账的话,在她突然抬起头的瞬间,全卡在了喉咙里,硬生生给噎了回去。
她今天显然精心打扮过,穿着一件红格子的呢子外套,头发梳得光溜溜的,辫子又粗又黑。可那张漂亮的、像刚剥壳鸡蛋似的脸上,没有往常那种凶巴巴的神气,也没有得意的笑。她的眼圈是红的,像抹了胭脂,但又比胭脂色沉得多。眼睛里汪着一层水光,亮得吓人,就那么直勾勾地瞪着我,嘴唇微微哆嗦着。
拧着我耳朵的手没松,反而更用力了些,指节都泛了白。
全场的声音,不知道什么时候低了下去,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俩身上,等着下一幕。
然后,我听见她的声音,带着明显的哽咽,却异常清晰地,穿透了那些窃窃私语和残留的笑声,砸进我耳朵里:
“我等了你八年……刘大年……”
一颗泪珠,毫无预兆地,就从她那双红通通的眼睛里滚落下来,顺着脸颊,划出一道亮晶晶的线。
“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?”
时间,好像就在那一瞬间,被冻住了。
周围所有的声音——风声,远处汽车的喇叭声,路人的议论声——全都潮水般退去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的世界里,只剩下她那双含泪的眼睛,和那句在我脑子里反复撞击的话。
八年。
我愣愣地看着她,看着她滚落的眼泪,看着她用力抿住却依旧微微颤抖的嘴唇,看着她拧着我耳朵、因为过于用力而指节发白的手。
那根扎在我心口很久的小钉子,好像就在这一刻,被这句话带着万钧之力,“砰”地一声,彻底钉了进去,钉到了最深处,带来一阵尖锐无比的酸胀痛楚。
八年。我们同年,她十八岁那年,两家人正式坐在一起,算是把这桩“娃娃亲”过了明路。那时候,我傻呵呵的,或许还有点隐秘的得意,毕竟郑丽华是村里最好看的姑娘。可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嫌她烦,觉得她管得宽,觉得她束缚了我的“自由”?
这八年,是她从十四岁水灵灵的小姑娘,等到二十二岁,成了村里人口中“老姑娘”的八年。我们那儿,姑娘家二十岁还没嫁,闲话就要起来了。而我,这个她名义上的未婚夫,却在盘算着怎么彻底逃离她,逃离那个有她的家。
我像个混账一样,忽略了她每次管我时,眼神里除了责备,是不是还有别的?忽略了她每次送我她偷偷做好的布鞋时,那微微泛红的脸颊。忽略了我娘每次欲言又止,最后只化成一声叹息:“丽华那孩子,心重……”
她拧着我耳朵的手,还没松。可那力道,似乎不像刚开始那样带着汹汹的气势了,反而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,带着细微的颤抖。
我那些冲到嘴边的、更伤人的话,什么“谁让你等”,什么“我才不娶你”,此刻像冰块塞满了我的口腔,冻得我舌头发麻,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脸上刚才被众人哄笑激起的燥热,迅速褪去,变成一种无地自容的滚烫。我甚至不敢再看她的眼睛,目光慌乱地垂下来,落在她那双黑色的、鞋尖沾了点灰的方口布鞋上。
周围安静得可怕。那些老同学,看热闹的,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,表情变得复杂,有人面面相觑,有人露出不忍的神色,有人悄悄别过头去。
这寂静比刚才的哄笑更让我难堪。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也许只有几秒钟,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。我听到自己干涩、沙哑,几乎不像我自己的声音,蚊子哼哼似的响起来:
“你……你先松开。”
郑丽华没动,眼泪还在掉,无声地,一颗接一颗。
我鼓足勇气,抬起眼皮,飞快地瞟了她一眼,又立刻垂下。喉咙像被砂纸磨过:“……这么多人看着呢。”
她依旧死死地盯着我,但那目光里的某种东西,好像在我的狼狈和沉默中,慢慢发生了变化。那强烈的委屈和控诉底下,一丝极其微弱的、习惯性的凶狠又浮了上来,虽然还浸泡在泪水里。
她吸了一下鼻子,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,却刻意拔高了一点,像是要维持住她最后的体面:“看?让他们看!刘大年,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,我……我拧掉你耳朵!”
这话听着凶,可配上她那通红的眼圈和没断线的眼泪,实在没什么威慑力,反而……反而让人心里堵得厉害。
旁边一个大概是徐志刚家的长辈,看不下去了,出声打圆场:“好了好了,丽华,有啥话好好说,大年这不是在这儿呢嘛?街上闹哄哄的,不像话……”
“就是,小两口有啥误会,说开就好了……”另一个女人也附和道。
郑丽华像是没听见,只是执拗地、泪眼模糊地看着我,等着我的“交代”。
我舔了舔干得起皮的嘴唇,感觉所有的血液都在往头顶涌。我知道,今天不给个说法,是过不去了。而且,就在她眼泪掉下来的那一刻,我心里某个坚固的东西,已经轰然倒塌。那所谓的“自由”,在“八年”这两个字面前,显得那么轻飘,那么可笑,那么自私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,带着烤鸭和街尘味道的空气呛得我有点想咳嗽。我抬起头,第一次真正地、直视着她的眼睛,那里面水光潋滟,映着我此刻惶惑又愧疚的脸。
“我……我没想逃。”我听见自己说,声音还是有些发虚,但至少清晰了些,“我……我就是出来……挣点钱。”
这话说出来,我自己都不信。
郑丽华的嘴角往下撇了撇,像是想冷笑,又更像想哭。她没说话。
我硬着头皮,继续往下编,或者说,往那可怜的真实上,盖一层遮羞布:“卖烤鸭……也挺好的,能……能自立。”
周围有人发出极轻的嗤笑声,但很快忍住了。
郑丽华还是不说话,只是看着我,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我彻底没辙了。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羞愧感攫住了我。我垮下肩膀,放弃了所有抵抗的姿态,连带着那只耳朵在她手里,也彻底卸了劲,声音低得几乎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:
“我……我跟你回去……还不行吗?”
这句话出口的瞬间,我清晰地看到,郑丽华眼睛里有什么东西,碎裂开了。不是愤怒,也不是委屈,而是一种……更深沉的,几乎是绝望的东西。她拧着我耳朵的手,终于,慢慢地,一点一点地,松开了。
耳朵上那阵紧箍感消失,带来一阵奇异的空落和微麻。
她没再看我,低下头,用手背狠狠地、粗鲁地擦了一把脸上的泪痕,把那张漂亮的脸蛋擦得有些发红。然后,她转过身,背对着我,肩膀几不可查地耸动了一下。
她没有说“好”,也没有说“不行”。
她就那么站着,红色的格子外套在午后的阳光下,显得有些刺眼。
周围的人群,见风波似乎暂时平息,开始慢慢地、意犹未尽地散去。有人拍拍我的肩膀,眼神意味深长。那个来拉我去喝酒的哥们儿,远远地冲我摇了摇头,叹了口气。
我僵在原地,看着她的背影,手足无措。烤鸭摊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旁,铁皮箱上油光凝结,刚才还觉得是自由象征的油腻腻的空气,此刻闻起来只剩下狼狈和窘迫。
她站了大概有一分钟,或者两分钟。然后,她猛地转过身,眼睛还是红的,但里面已经没有眼泪了,只剩下一种疲惫的、带着点狠劲的平静。
她几步走到我的烤鸭摊前,目光扫过那几只剩下的烤鸭,又扫过我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,最后落在我脸上。
“收拾东西。”她说,声音不高,带着哭过后的沙哑,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我愣了一下。
“愣着干什么?”她眉头习惯性地一蹙,那点熟悉的、让我心烦又此刻让我莫名心定的“凶”气又回来了些许,“把这些破烂都收拾好!蹬上你的车,跟我回去!”
“回……回村?”我下意识地问。
“不然呢?”她瞪着我,“你还想留在这儿继续你的‘大业’?”
我哑口无言,默默地开始收拾。把砧板、刀具收到箱子里,把炭炉盖灭。动作有些迟缓,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一团。
她就在旁边看着,也不帮忙,抱着胳膊,像监工。等我笨手笨脚地把所有东西都归置好,推起自行车时,她走上前,一把将我推开些:“笨死你算了!”
然后,她极其利落地检查了一下捆扎的绳子,又伸手进铁皮箱子里,摸了摸里面烤鸭的温度,嘀咕了一句:“都凉透了,糟蹋东西。”
我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,跟在她身后。她迈开步子,径直朝城外我们村的方向走去,步子迈得又快又稳,那根粗黑的大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。
我推着沉重的、叮当作响的自行车,跟在她后面几步远的地方。午后的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她的影子走在前面,我的影子在后面追着,时而又重叠在一起。
一路上,我们谁都没说话。
只有自行车轮子轧过土路的“沙沙”声,还有远处田野里传来的几声鸟叫。
风吹过来,带着麦苗返青的清新气息,吹动她额前的几缕碎发,也吹动我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烤鸭油腻味。
我偷偷看着她的背影,那挺得笔直的脊梁,那偶尔抬起用手背蹭一下眼角的小动作。心里那阵尖锐的酸胀感,一直没有消退,反而像水波一样,一圈一圈地荡漾开,淹没了之前的烦躁、抗拒和那点可笑的、自以为是的自由。
八年。
这两个字,像烙印,烫在我的心口上。
我好像,到今天,才第一次,真正地、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我躲了又躲,烦了又烦的,我的未婚妻。
路还很长,从县城到村里,三十里地,够我推着这辆沉重的破车,想很久,很久。
(第一章完)
#优质图文扶持计划#配资网站查询
发布于:陕西省辉煌优配吧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